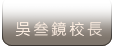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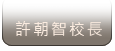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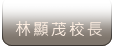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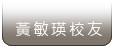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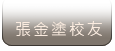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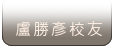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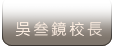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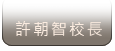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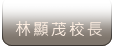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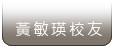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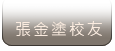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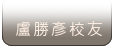 |
回首當年話雄工- 黃敏英先生 黃敏英先生筆(雄工第四屆機械科校友)
黃敏英先生於雄工求學模樣
一、前言 「雄工」,這是多麼熟悉,多麼親切的名字!不錯,「雄工」正是我的母校! 他們伴我度過青少年時代最珍貴的六年黃金歲月,一提到「雄工」,難免令我憶起六十年前的種種情景,也令我從內心浮現無比的歡喜與辛酸!畢竟六十年了,以一個人生來說,足足過了一甲子了,現在喜逢六時週年校慶,母校要求我們早期的同學來敘說當年的雄工,其意義重大,聽了真的既高興又欣慰,可是當心情靜下來時,又陷入不知從何談起的惶恐。 二、雄工的成立 那是1942年(民國31年)的三月,日本政府統治下的台灣總督府未考量厚植日本的工業實力,把目標設定在擁有廣大海洋資源及豐富石油、林木等資源的南洋群島(指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新幾內亞、泰國、帛琉、蘇格門群島等)進行 儲備一批強而有力的工業技術生力軍。經過相當周詳的規劃和長時間的思考,最後決定在工業重鎮之都-高雄創立一所州立(官立)高雄工業學校,這就是「雄工」創立的由來。 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北有台北工業學校,南有高雄工業學校,南北兩校相互照應,也是當時日本教育界的一大理想;而且當時的高雄已經有號稱東南亞最大且頗負盛名的淺野水泥(台灣水泥前身)、高雄煉油(中油前身)、台灣機械(有造船、鑄造、加工機械三廠、戲台機前身)、南日本化學(台肥前身)以及台灣鋁業等重工業,擁有引導工業往上提昇的條件,所以雄工創校是符合各界的企望與滿足日本政府需求的。 三、早期雄工招生情況 雄工創立初期,日本政府再高雄市東郊灣仔內規劃了一筆60萬坪的農地作為雄工建校用地,這是當時全台灣各中等校最寬大完整的校地。日本政府非常慎重遴選了一位特任官---宮本清利博士(係日本著名的教育家,也是專業的高分子化學博士,在學術界我崇高的地位)來擔任首任校長,並著手規劃建校與招生事宜。 1942年春季開始招募學生,公告一發出,立即引起社會以及各校學生們的注意,四面八方的學生莫不仰木雄工的校名,相率約群來應考,甚至很多已經在其他中學就讀的學生也甘願放棄中學生身份前來參加入學考試,連同一般國小生畢業,形成空前激烈的申學競爭。當時雄工的新生錄取率是 21:1,一般中學則是6:1比例,通過嚴格的升學洗禮,能進入雄工的學生,都是非常有氣質、有智慧,且學科優秀的人才。 以我自己所屬的第四屆機械科生而言,雄工畢業後,全班共53人,繼續升學者台大有七人,成大有三人,中興有二人,專科有五人,參加全國性就業特考及格者有十四人,可說成績非凡,個個在社會上都有相當不錯的成就。 四、雄工的特殊教育制度與雄工的校徽意義 那時候的日本教育政策,有一條殖民教育不合理的規定,就是新生錄取每科學生必須維持日本3人:台灣1人的比例,所以當我們進入校門,老師點名時,始知台灣人僅有十來名而已,但是當時我們不明白不合哩,只會埋怨雄工難考,慶幸自己幸運考上,一方面也未眾多被擠出門外的學子難過。雄工在當時號稱是全台灣最完善的工業學校搖籃,設有機械科、電子科、化工科、建築科、圖木科等五科,之外,為配合日本教育發展航空事業,以其支援日本從事二次大戰的戰備力量,還增設其他工業學校所沒有的航空機械科及金屬材料科,所以總共有七科,是當時台灣最完善的工業學校。 當時的雄工校徽展現出它的大志,校徽的中間採用十字星圖樣,表示雄工是屹立於日本最南端的工業學校,雄工是背著南進使命,負擔繼往開來,前進南洋廣大地域所開發的任務而來的,而在南十字星圖樣的兩旁則採用旺盛蓬勃的海洋來展示它的雄心大志,這也象徵台灣四面臨海,高雄又是大的工商港口,在這個無盡資源的海洋中,雄工具有無限生機與開展空間,所以這個校徽甚得全體師生喜愛。 當時雄工初創,即面臨八年抗戰及二次世界大戰的衝擊,所以學校的行政與教學制度也必須因應日本政府的需要而有所調整。我記得當戰爭接近尾聲,盟軍反擊越激烈時,三至四年級高年級同就被日本政府以全國性學徒總動員的號召徵調去服學徒兵役,而一、二年級生也要響應學徒動員,被徵召參加學徒義工隊,做為時三週的挖掘山洞工作,這一段戰爭期間,學校無法正常授課,因盟軍的反攻越來越激烈,密度也增加,學校被迫採取疏散到農村上課,且一週只上課兩天,老師遠從高雄下鄉授課,我是被編到屏東縣西勢村香蕉檢查所上課,所以印象很深刻。雄工設立之初,是完整的五年一貫教育學制,也是甲種工業學校,光復之初,剛好有一到四年級,為了配合中國教育制度,四年級生劃歸高級部一年級生,其他則列入初級部一至三年級,這是很特殊的現象。 五、台灣光復初期的雄工 當時高雄的情況最危急,因政府下令高雄要塞司令出動軍人鎮壓,所以到處都可看見鎮壓後的斑斑血跡,實在廖不忍賭。當時尚有多位日籍老師留台未返日本,外面風聲又對日人不利,因此雄工學生自治會由高年級三至四年級生志願住校保護老師,我們低年級同學則經老師和高年級生再三告誡:回家!不要出外看熱鬧,不要惹事生非!規定大家待在家中多看書,多孝順父母,做家事。那時我住鳳山,甚無聊,常與兩位同學相約前往大貝湖釣魚,平安度過了黑暗的228 。 八、時代交接初期的求學辛酸 當時學生沒有課本,大家只好專心快速做筆記,如此不正常的上課情形所產生的副作用,就是每個學生所作筆記內容有所出入,經常鬧笑話。而只用筆記上課的方式帶給學生很多壓力,每人下課回到家,尚須花費很多時間重新整理筆記,謄寫完整內容,所以求學辛酸一言難盡。後來我們班提出建議,請老師提供講稿,由班上學生以自助方式輪流刻鋼版,再加以油印分發,才得到解決,雖然求學做筆記很辛苦,我還是很感謝在求學過程中,有這麼一段時問來鍛鍊速記能力,爾後在社會上服務時,幫了我很大的忙。 九、雄工與商工專修學校合併 台灣光復之初,高雄市獅甲地區有一所高雄商工專修學校,學制三年畢業,屬於乙種工業學校。該校學生本來眾多複雜,素質並非上選,加上管理不善,經常鬧事而不上課,這形同罷課一樣的行為,時處228後戒嚴時期,是非常嚴重的罪行,迫使學校與政府機關不得不採取非常手段,下令學校封閉停課,並立即進行規劃與雄工合併事宜,其方法就是經意願調查後,將專校師生移併雄工管理。 如此一來,雄工的學生在一夜之問暴增不少,我們這一班由原來的24名小班,一下子增為74名,因為併校學生的素質與學力與我們有相當的差距,守法精神也差,所以上課必須為這些併校生從頭開始授課。但是無論老師如何努力教導,併校生的成績都無法趕上水準,所以產生很多後遺症。第一年本班就有30名留級生,可說破了雄工紀錄;另方面,功課不好、品行不佳的併校生,暗中到外結社滋事,經常與原來雄工學生打群架,甚至修理恐嚇其它學校的學生,社會上逐漸傳出雄工的惡霸勢力與拳頭文化,各個學校視雄工學生如猛獸,不敢接近,這是雄工最黑暗的時期。 另外,這批併校畢業生紛紛向外宣稱他們是雄工的正統生,其實他們的校史比雄工早四年,這種啼笑皆非的論調把辛苦建立起來的雄工校風破壞無遺,使雄工無法獲得一般社會人士的認同,前來應考的學生素質也直線下降,這是很令人痛心的事。 十、雄工的重新振起· 繼往開來 十一、結語 回憶至此,念頭一轉,人生有如走馬燈,六十幾年的歲月彷彿如昨日一般,歷歷飛逝,年輕時代的我與過去的雄工雖然漸行漸遠,我對雄工仍然充滿懷念,衷心祝福母校的學弟妹們,能繼往開來,將當年的優良校風發揚光大,讓雄工成為南台灣工業職校的永遠指標!
|